跟大家说一件事。
7月16日晚18:00-22:00,我们会办一场特别的直播,罗振宇将会问万维钢十个有关未来的问题。
这十个问题包括但不限于“AI会怎么改变我们的读书方式?”“AI时代,该怎么教育孩子?”“美国现在的创业环境怎么样?跟上一轮有什么区别”“现在出国留学还是个好选择吗”。
这些问题希望能与你们一起探讨和交流。
点击下方直播预约链接,相信有些问题,你也将会获得答案!
来源:《万维钢·精英日课6》
作者:万维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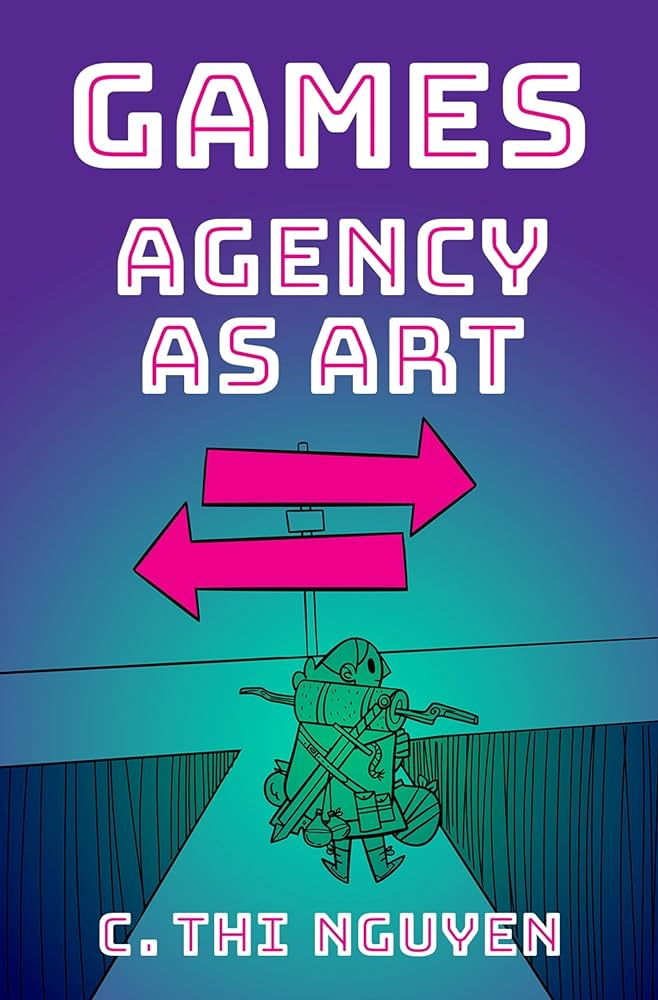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万维钢·精英日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