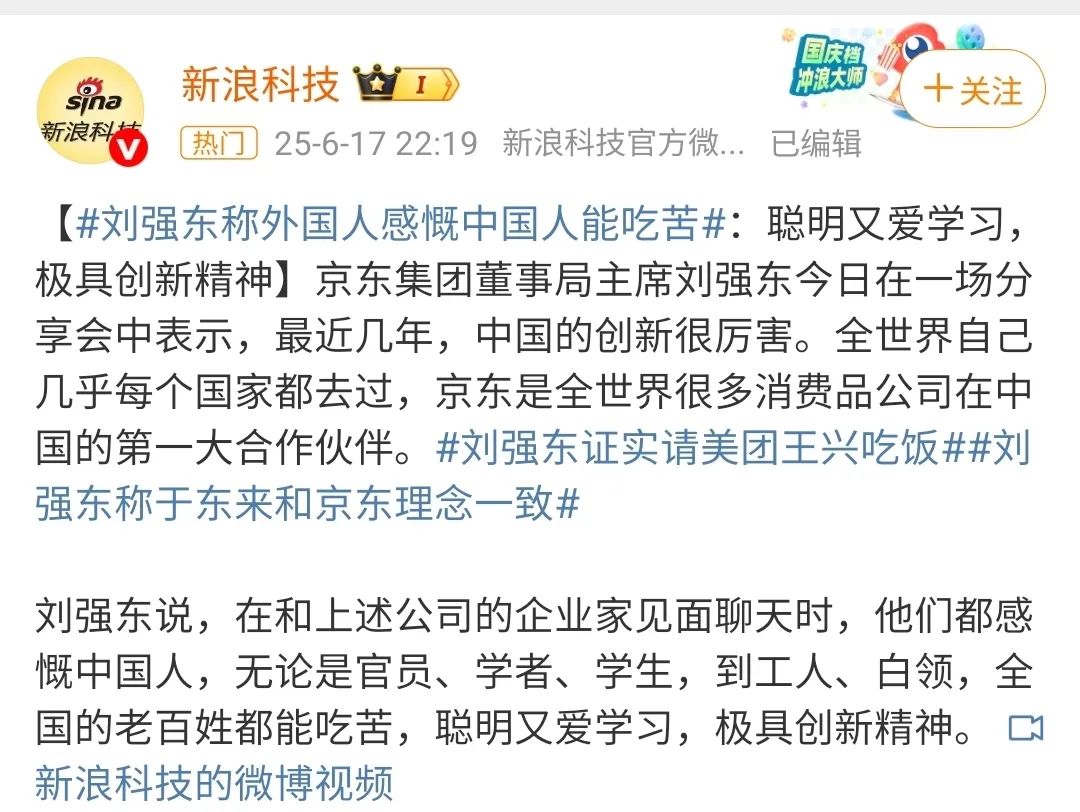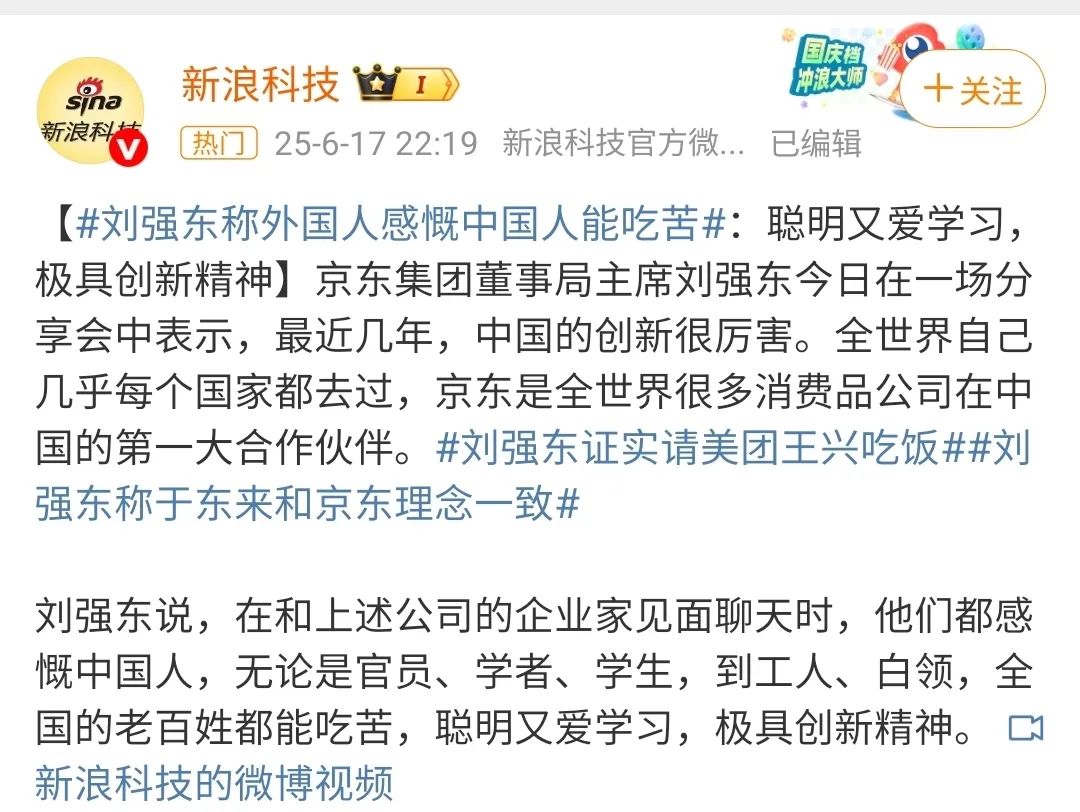勤劳吃苦,既不是中国人的特征,也不是富裕的原因
Author: 漫天雪798
| Origin link:
wechat link
这个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在办企业上他至今算一个成功者,然而在舆论观念传播上,他是一剂毒药。他反复传播的,都是反市场的观念,或者错误归因的、煽动性的胡言乱语。
我们首先要指出:吃苦本身并不值得追求,它甚至都算不上一个值得称赞的美德。如果目的错了,吃苦就是害人;如果手段错了,吃苦就毫无意义;如果再把吃苦上升到哲学意义,那就更是贻害无穷。
一个公务员如果非常吃苦,
那就可能在危害社会。
像雍正皇帝一样把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政出一门,利出一孔,那就是把社会变成一座巨型监狱;一个税务局的公务员非常“吃苦”地收税,就是在毁灭资本,阻碍经济进步;本杰明·富兰克林办印刷厂,通过自己的关系承揽到了大陆会议颁发的印钞特权,然后“勤劳奋斗”地昼夜印钞票,把大陆币印得一文不值,把民众财富劫掠一空。
如果目的正确,却不知道采用什么正确的手段去实现,那么吃苦往好了说就是在做无用功,往坏了说就是人类的一桩愚行。“用勺子挖运河”,比用现代化设备去挖,要吃苦得多,可是那就是愚蠢至极。天天“吃苦耐劳”,生产一大堆消费者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然后说自己产能过剩了,那根本就是错误的生产,就是在毁灭财富。
把吃苦再上升到哲学高度,那就是清教徒专制主义,任何享乐都为教法所不容,都在道德上受到攻击。还是这位“坏老头”本杰明·富兰克林,指责殖民地的人睡眠的时间太多,并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对他来说,的确是如此。清教徒专制分子颁布“星期日蓝法”,要求星期日必须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在劳作中度过,任何享乐与休闲都是对上帝的背叛。
埃米尔·考德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考证,西班牙经院学派和欧陆理性主义传统为什么阐释了主观价值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不排斥人们追求享乐的主观偏好。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什么认为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因为他们都是新教徒,且信奉英伦经验主义,于是自然地坚信“劳动价值论”。他们是老马的导师。这种理论贻害无穷,是“人类的智识丑闻”(霍普语),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
综上,勤劳,吃苦,不应当被赋予过多的道德意涵。人必然要吃苦,因为人面临着稀缺性的约束,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从目的手段框架分析,它更多是一种个人偏好。如果一个人把苦行修炼当成精神追求,这是他的个人价值,没什么好评价的。如果一个人要实现某种目标,付出了艰辛和努力,那是它实现目的的手段。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从目标实现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就像我喜欢经济学,每天读书到半夜,你认为我很勤奋很吃苦,但是我觉得我很快乐。
人从目的中获得满足,
吃苦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快乐,也没几个人喜欢去吃苦,因为劳动有负效用。假若还有人要求别人为了吃苦而吃苦,那更多的可能是一种PUA控制术和道德枷锁。
市场经济发明的各种机械设备和家用电器,恰恰就是为了把人从吃苦中解放出来,享受更多的休闲;为人父母,奋斗搞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变好,让孩子不用吃这些苦。
那勤劳吃苦,是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品质,或者是所谓的“民族性”呢?
古典经济学家发起了智识革命,催生了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英国人非常能吃苦,以至于一帮伪善的学者批判他们的“血汗工厂”和童工制。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人,更是勤劳吃苦和勇敢无畏的典范,他们不畏艰险,翻越内华达山脉和沙漠沼泽,来到西部讨生活,拓殖开垦淘金,“全年无休昼夜不息”。
改革开放前,人们个个磨洋工,在公社里得过且过,能少干就少干,能跟公社领导搞好关系就能多分一点粮,结果搞得人人吃不饱。计划时代,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尾巴,出个村子要开证明,想要到城市里讨生活都没门,想勤劳而不得。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个个劲头十足,玩命干活,可以进城打工了,于是深圳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老板和劳动者干得热火朝天,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难道几十年间,中国人发生了基因突变,民族性被改良了?
一个更加自由的、产权有保障的市场环境,人就自然在勤劳吃苦与休闲享受之间进行边际选择,他就会无需皮鞭抽打而自愿地去“吃苦”。因为人的欲望总是不满足,总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办法就是瞄准目标,勤劳奋斗,现在吃苦,是为了未来多享受。
如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村子都出不了,你就想勤劳而不得;如果产权没有保障,想与人交换不被允许,生产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那么为什么要勤劳?
欧洲人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懒惰?不是他们民族性有问题,也不是他们骨子里就是懒,而是社民主义福利国家摧毁了人的奋斗精神,进一步地固化了阶层等级。
当一个法国人辛勤打拼的财富,被拿走50%以上养别人的父母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勤奋努力呢?当你不需要勤奋努力,就能吃不饱饿不死的时候,工作的价值下降,休闲的价值上升,那何不躺平呢?当一个父亲辛勤打拼,想要给孩子留下更多财富,却要征收高额遗产税,那他不如死之前吃干喝净,免得给孩子增加税收负担。当你想干一件服务消费者的事情,做一点小生意当一个小老板,实现人生的逆袭时,
产品质量的、环境保护的、劳动保护的,管制和干预丛生,暴力机器处处设限,那就没有小企业成长的空间,也没有阶层跃升的可能,这就是一个大企业在壁垒下高枕无忧,进而阶层固化的社会。
甚至,当一个人想要下午五点后和周末开门营业,它不允许,那么勤劳奋斗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政府能发放多少福利,就能养多少懒汉;能发多少失业救济金,就能增加多少失业。正是种种侵犯产权的福利政策,让人们变得养尊处优懒惰如猪且吃嗟来之食而没有羞耻感。当管制干预让人们想勤劳而不被允许,那就是整个社会衰落和崩坏之时。
所以,勤劳与否,吃苦与否,都跟民族性没有关系,它就是人们观念变化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
至于把勤劳吃苦,当成是物质丰裕的原因,更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无知,是错误归因。
让人们变得富裕的,勤劳吃苦既算不上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
荒岛上的鲁滨逊,很勤劳,能吃苦,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比我们现代人还多,他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吗?
我们的祖辈,论勤劳奋斗和吃苦精神,绝对超过了我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无休,能实现物质丰裕吗?
非洲普通民众即便工作的时间很长,再吃苦耐劳,能和我们一样开上便宜的汽车、吃上便宜的外卖、用上廉价的电器设备吗?
鲁滨逊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多的鱼,满足日常所需没有性命之忧,腾出了足够的时间制造捕鱼设备后,才能走向富足之路;假如荒岛上又来了一个星期五,他擅长种粮食,两个人交换,他们俩人就都有了鱼和粮食,生活就会大大改善。
鲁滨逊产出大于消费而结余下来的鱼,就是他的储蓄。只有在这些储蓄的支撑下,他才能去制造捕鱼设备而不至于饿死。那些捕鱼设备,就是他的资本品。
我们的祖辈之所以如此勤劳也没法过上富足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因此劳动生产力低下,产出只够消费,就没有技术进步的可能。
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间,人类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被许多人吹嘘的所谓大唐盛世大宋雄风中,离京城几里远,人相食、易子而食现象不绝于史书,还是因为父母没有资本积累。
在古代,淘汰老弱病残,跟动物世界一模一样,人们不会有多少同情,因为他们不增加资本而消耗资本,会威胁其他人的生存。
决定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的,是人均资本存量。资本多了,才能启动较长过程的迂回生产,才能提升劳动生产力,进而一方面提高实际工资率,另一方面增加供给、降低物价。由此,实际购买力提高,生活水平节节攀升。
任何一个人的储蓄增加,都会转化为投资,都将带来生产力的进步,所有人都将从资本增加中受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开始资本积累之时。
因为即便自己的技能并没有进步,随着资本增加、先进的技术设备的使用,也能水涨船高地提升自己的工资率。
三和大神既
不勤劳、也不爱吃苦,为什么每周
只用工作一天就可以活下去?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让他的日工资提高,同时物价下降,他的购买力增强了,所以工作一天就可以满足一周生活所需。
要想资本不断积累,唯一的办法就是保障产权,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只有产权有保障,人们才会降低时间偏好,增加资本积累而不是吃干喝净,由此,才会启动一轮又一轮技术进步和迂回生产的进程,不断地面向长远的未来而生产,增加未来的供给。
只有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让每个人拥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实现阶层跃升,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消费者喜欢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只要你判断对了,消费者就给你慷慨的金钱投票让你盈利。这里没有世袭、没有种姓、没有贵族、没有等级,没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一切凭借服务消费者的能力取胜,每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需要谁分配,不需要谁安排,消费者需求就是最好的指挥棒,消费者投票就是最佳的奖赏。
也正是市场经济的职业自由,让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让分工合作、
交换共赢
成为可能,实现了最大化的产出,造福于社会的每个成员,
每个人都由此享受到了丰裕的物质供应。
如果你又懒又挫,那你就一定要支持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节节攀升,收入提高而物价降低,你才能活下去,在计划经济中,这种人要么被人在皮鞭抽打下“勤劳”,仰赖他人的恩赐而奴颜婢膝,要么就唯有死路一条。
如果你关心弱势群体,那也要支持市场经济。老弱病残为什么现在也能活下来?不是因为法定救济——它也来自对市场资本的征收——而是因为资本积累足够雄厚,可以支撑他们的消耗而不至于威胁人们的生存。老弱病残却依然能活下来,是文明社会的现象,是一个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特有的现象。
如果你关心共同富裕,那更要支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就是造福于贫困阶层、而不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制度。自由市场倾向于为它的参与者带来富裕,市场上的暴力干预和霸权性社会倾向于导致普遍的贫困。自由社会、自由市场,提供了减少或者消除贫困的唯一手段,并带来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