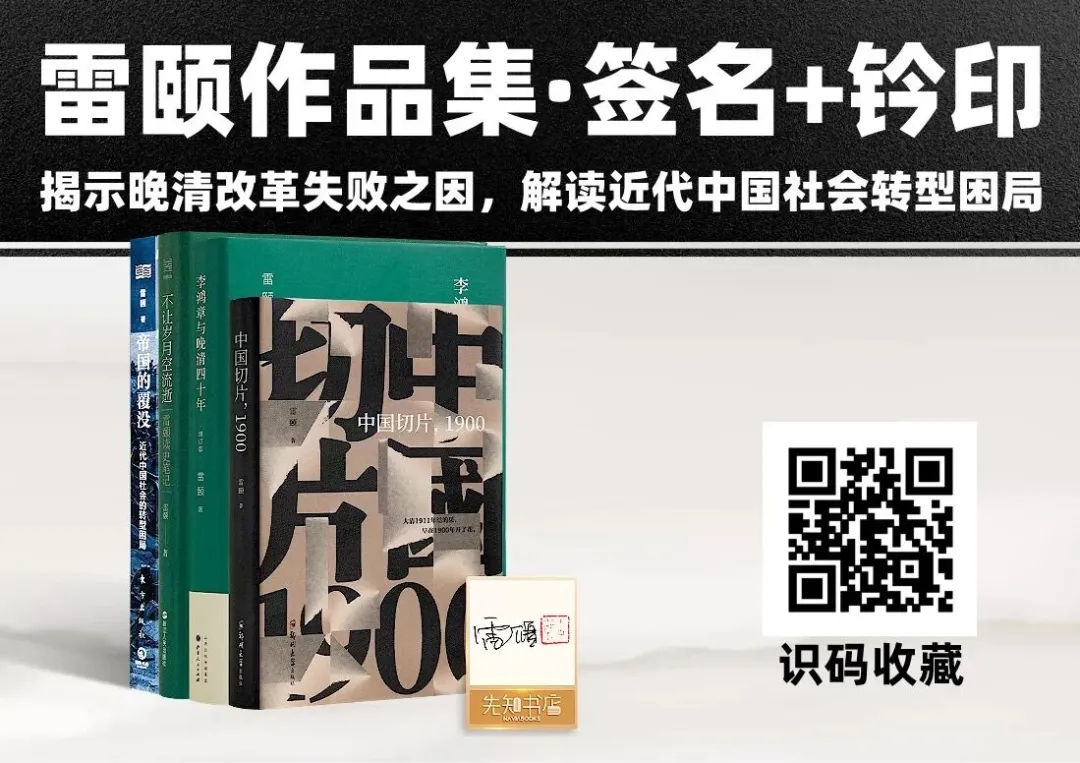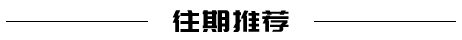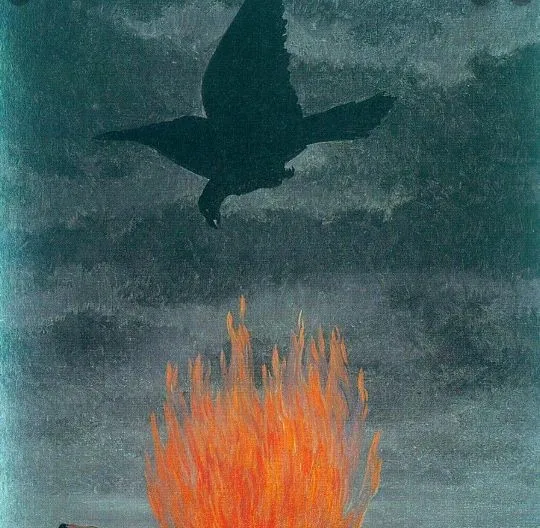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
“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自己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外,并不知道关于政治和世界更多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一秒钟之内就像疯了似的。我感到吃惊。我浑身不寒而栗。
因为我感到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市镇,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
当接着映出其他画面时,观众又把刚才的一切全都忘记,喜剧正片放映时个个捧腹大笑,直拍大腿,劈啪作响。但茨威格却再也不能平静:
“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做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动起来。”
闭塞小城低层百姓这短短“一秒钟”,却是掌控着各种媒介的执政者长期教育的结果。
战争爆发后,使茨威格更感震惊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也以狂热的言词宣扬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绝大多数作家都以狂热的文字鼓吹“为祖国而战”,“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
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
而“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他们唯一的“高论”就是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人民力量的“洗礼”。
茨威格的熟人、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
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
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一样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

这种貌似“崇高”的“道德优势”不仅为群体的狂热火上浇油,而且使反对者居于“道德劣势”而难以启齿,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而不敢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为却勇而为之,积极著文反战,还用戏剧的形式描写、肯定在狂热的时刻被认为是软弱的胆小鬼而遭人蔑视的“失败主义者”。
不过,茨威格马上发现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至于他也常常怀疑究竟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抑或确是别人聪明自己发了疯。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他一同跳动。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
“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
茨威格发表了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表示反对战争、与敌国的朋友仍保持原来的朋友关系;罗曼·罗兰发表了《超脱于混战之上》的反战文章,抨击国家间的仇恨精神,要求艺术家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
由于战时媒体的审查制度,敌国的作品很难发表,本国读者很难读到这些反战作品。因此,他们甚至以写“批判文章”的方式让本国人民也能看到这些敌国思想家写的反战文章。在他们周围,人数不多的反战作家渐渐团聚起来。
生长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此时尚属籍籍无名之辈,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但在小说《往事一页》中也甘冒触犯众怒之险,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小的鞋匠,修鞋铺就开在皇宫面前的广场上。一天清晨开门一看,发现全城不知何时已被来自远方的游牧民族占领。侵略者虽是为了皇宫中的金银财宝而来,但烧杀抢掠从平民开始,鞋匠、肉贩等都备受骚扰。
这时,“我”来到皇宫门口,看到皇帝站在一扇窗后。“平常,他可从不到宫内靠广场的房间来,而总是生活在最里面的花园中”,这次却垂头丧气地站在靠广场的窗后,眼睁睁地看着宫前发生的事情。
最终,不堪种种磨难之苦的平头百姓们聚在一起互相问道:
“我们要承受这样的负担和磨难到什么时候呢?皇上的宫殿把游牧人吸引来,他却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宫门始终闭着;往常耀武扬威地出出进进的卫队,眼下全待在装了铁栅的窗户后面。拯救祖国的事结果全得由我们工匠和商人来干,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这篇寓言性小说发表于191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千千万万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为国家浴血奋战,为“救国”而英勇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是气焰万丈。卡夫卡显然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以小说来消解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
以一篇全文还不到两千字的小说消解千百万人着魔般亢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无疑连杯水车薪都不如,但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仅表明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性,更表现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退一步说,至少是作家个人在大是大非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使人久久回味。这篇小说起码从某一角度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
在“天下”“兴”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从不认为“匹夫有责”、“与有荣焉”,自然也就不许匹夫有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每当“天下”将“亡”的时候,皇帝们总是疾呼“匹夫有责”,仿佛事之所以至此人人都要承担一份罪责,匹夫自然就有承担“救亡”重担的责任与义务。
话当然要说回来,如果“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而是所有匹夫也都享有一份权利的“天下”,那么自然应担起“救亡”之责;不过如果“天下”为某“一姓”之私物,当皇帝大呼“匹夫有责”时,鞋匠、肉贩……所有平民百姓确应冷静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责”。
很可能,“拯救祖国”“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卡氏此言,可谓语重心长。


本文作者雷颐老师是当代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在其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1900:中国切片》《帝国的覆灭》清末三部曲以及《不让岁月空流逝 | 雷颐读史笔记》
中,对晚清覆灭史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逻辑,晚清改革派的生存处境,
领导者在大动荡中的通权达变和权术手腕,都生动毕现,更是入骨三分的揭示了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权力秘密。
吴晓波: 在我心目中,雷颐先生是国内清末史研究“第一人”。
读雷颐老师的著作,能深刻地体会到:读历史,也是读现实。以历史为镜,才能打破黑暗与迷途,烛照未来。因深知雷颐作品价值,特别邀请 雷颐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钤印(4册全签),签名版数量不多,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